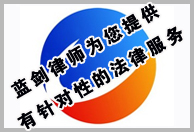解读法条间存在的“逻辑冲突”【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副院长】
根据刑法总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不具备法定减轻处罚情节的被告人予以减轻处罚的案件,必须报最高法院核准。依此规定可以合乎逻辑地推导出:对既不具备法
定减轻处罚情节,又无法定免除处罚情节的被告人予以免除处罚的案件,就更应报最高法院核准。但根据刑法总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对于没有法定免除处罚情节的被告人如果认为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予以免除处罚,法律并没有规定要报最高法院核准。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在这两个法条之间存在“逻辑冲突”呢?2005年9月5日《人民法院报》刊登梁剑《如何处理法条与逻辑之间的冲突》一文(下称“梁文”),肯定了“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的一些规定与做法存在违背逻辑的地方”,并且提出“既然法律对于减轻处罚、免除处罚的条件均作出了明文的规定,那么,我们在适用法律时就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法官在量刑时,即使被告人没有法定免除处罚情节,只要认为案件中的被告人的确符合免予刑事处罚的适用条件,就可以对被告人大胆地适用免予刑事处罚,而不必报最高法院核准。”笔者认为这种法条间存在“逻辑冲突”的观点值得商榷:
一是减轻处罚与免除处罚的性质不同,减轻处罚是认定构成犯罪后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判处刑罚;免除处罚是认定构成犯罪后不处罚。判处刑罚与不处罚是有原则区别的,尤其是某些严重犯罪,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法定最低刑很高,如“梁文”所谈及的张某绑架案,法定最低刑是十年有期徒刑,对被告人是做减轻处罚,还是做免除处罚,结果差别很大。在案件不具备法定减轻和免除处罚情节的情况下,如果减轻处罚,根据法律的规定不仅办案法官没有权力,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也没有权力,只有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而如果选择宽于减轻处罚的免除处罚,按照“逻辑冲突”观点简单认为的那样合议庭可以依法直接做出,而不用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不仅仅是逻辑冲突的问题,更重要是影响执法的统一,显失法律的衡平;
二是刑法总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其立法价值在于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维护罪刑法定原则。如果刑法总则第三十七条与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存在着逻辑冲突,不仅使刑法总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失去了立法价值,而且有可能导致刑事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把本应报最高法院核准做减轻处罚的案件,而做免除处罚,造成在实践中执法的不统一和法官恣意擅断的恶果;
三是如果刑事立法真的存在“逻辑冲突”,就意味着刑事立法存在严重疏漏,要么予以修改,要么通过作出司法解释的形式予以弥补,而不能留下如此严重疏漏让法官在司法实践中任意理解和适用,这有损于法律的权威和严肃。但是,到目前为止,立法机关和最高法院并没有对刑法总则第三十七条做出否定性评价或限制性的规定。
基于以上分析,说明“逻辑冲突”的观点并不成立,是对立法精神误读。笔者认为,纵观我国刑事立法结构、体系,刑法总则第三十七条与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具有内在联系,刑法总则第三十七条直接适用于个案,在特定的情况下要受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限制。主要理由阐述如下:
第一,法官所享有的刑事自由裁量权,是指在刑事审判中法官在一个合理范围内对案件自由地作出主观判断的权力,包括对案件事实如何认定、对于临界行为如何定性,以及如何合理量刑等问题进行处理等。从理论上讲,刑事自由裁量权,是有条件的、是要受到限制的。这个条件和限制就是必须“在一个合理范围内行使”。这个“合理范围”应是基于刑事法律的规定和刑事法律所蕴含的原则和精神,它是客观的,可衡量、把握和操作的,而不应是法官的主观臆断。具体到司法实践,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要受到如下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定的限制:从宏观上讲要受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原则的限制,即必须遵循罪之法定、罪名法定、刑之法定的原则;从微观上讲对具体案件的被告人裁量刑罚要受刑法分则规定的法定刑的限制;要突破法定刑,就要受刑法总则规定的法定量刑情节的限制;不具备法定减轻处罚的要减轻处罚要受刑法总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限制。由此形成对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法律约束。刑法总则第三十七条规定了“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从形式上看,法律并没规定适用的具体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官可以仅凭主观判断,不受限制地自由适用这一法律规定。理由是:
第二,从立法上看,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三类事由可以适用免除处罚:一是刑法总则针对犯罪的具体情节作出的“可以”或“应当”免除处罚的规定,这些具体情节包括:预备犯、中止犯、从犯、胁从犯、自首、立功及防卫过当和紧急避险过当构成犯罪等情节;二是刑法分则针对具体犯罪的特殊情节做出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的规定,包括刑法分则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的行贿人在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第三百五十一条规定的非法种植罂粟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在收获前自动铲除的、第三百八十三条规定的个人贪污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1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第三百九十条规定的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第三百九十二条规定的介绍贿赂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介绍贿赂行为的;三是刑法总则针对犯罪的综合情节做出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的规定,这就是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以上三类事由前两类是具体的、明确的,在执行中不发生争议。只有刑法总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则是原则的,看似法条没有具体规定适用的条件,可以由法官内心确信,自由裁量。实际是有条件的,只不过这种条件没有用具体文字明确规定在具体法条之中,而是蕴含在刑事立法结构和体系之中。
第三,纵观我国刑法分则立法结构,对大部分犯罪依犯罪情节分别规定了基本犯罪构成和加重(分为结果加重和情节加重)犯罪构成,并相应规定了基本罪法定刑幅度和加重罪法定刑幅度。对基本罪法定刑幅度的规定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法定刑幅度从高到低界定,如刑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的丢失枪支不报罪的法定刑幅度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法分则对社会危害性相对较轻的犯罪一般都采用这种从高到低的方法界定法定刑的幅度,只有故意杀人罪是例外;另一种是法定刑幅度从低到高界定,例如“梁文”涉及的案例绑架罪,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的法定刑幅度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采取这种方法规定法定刑的一般都是社会危害性相对较重的犯罪。再细分,从高到低界定法定刑幅度的,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所规定的法定刑幅度下限包含了刑罚体系主刑最低的刑种(管制),如诈骗罪,刑法规定的基本犯罪构成的法定刑幅度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另一种没有包括主刑最低的刑种,如前述的刑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的丢失枪支不报罪,法定刑幅度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法定最低刑不包括管制这一主刑最低刑种。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规律性认识:根据刑法分则对法定刑幅度规定的不同,有三种情况的犯罪存在减轻处罚的刑罚空间,1.适用加重罪法定刑幅度的犯罪。因为加重罪法定刑幅度是建立在基本罪法定刑幅度之上的。所以,基本罪法定刑都可成为该罪减轻处罚的刑罚空间;2.适用从低到高界定法定刑幅度的犯罪。因为我国刑法分则对犯罪采取从低到高界定法定刑幅度的,最低刑都是从三年有期徒刑起刑。所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都是减轻处罚的刑罚空间;3.适用从高到低界定法定刑幅度的犯罪,法定最低刑中没有包括主刑最低刑种(管制)的,管制刑就是减轻处罚的刑罚空间。只有在从高到低界定法定刑幅度中包括主刑最低刑种(管制)的,没有减轻处罚的空间。因为,管制刑是法定最低刑,法定最低刑以下就没有可判的刑罚(主刑)了。分析刑法分则对法定刑幅度规定呈现的这种特点,再结合刑法总则第三十七条和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笔者认为,对不具有法定减轻处罚和免除处罚情节的被告人予以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应遵守以下裁判规则:
1.法律规定的法定刑幅度存在减轻处罚的刑罚空间的,法官如果拟对被告人做减轻处罚,依法就要报最高法院核准;法官如果拟对被告人做宽于减轻处罚的免除处罚,因为中间跨着减轻处罚的刑罚空间,这种情况下的免除处罚,实际是在减轻处罚基础上做出的,理应受刑法总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制约,也要报最高法院核准。
2.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幅度不存在减轻处罚刑罚空间的犯罪,如果认为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才可直接适用刑法总则第三十七条,对被告人做免除处罚,而不必报最高法院核准。其一,这样做并不违背刑法总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立法精神,因为,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幅度不存在减轻处罚刑罚空间的犯罪;其二,这种情况下的犯罪均是轻微犯罪,即法定最低刑可以判处管制刑的犯罪,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节和社会危害性认为判处管制刑罚仍觉得过重的,只有适用刑法总则第37条判处免予刑事处罚了,这样做是法官对刑事自由裁量权的正当行使。
3.对适用加重罪法定刑幅度的犯罪和法定最低刑相对较高的犯罪(如前述绑架罪)在不具备具体的法定免除处罚情节的情况下,一般不应直接适用刑法总则第三十七条对被告人做宽于减轻处罚的免除处罚。这是因为,适用加重罪法定刑幅度的犯罪和法定最低刑相对较高的犯罪,构成这种罪的本身就说明被告人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性的严重。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性严重的犯罪又认定“犯罪情节轻微”而判处免除处罚,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也违背刑事立法的基本精神。当然如果案件特殊,确需做出免除处罚的必须报最高法院核准。
需要说明的是,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幅度是否包括附加刑不影响减轻处罚刑罚空间有无的判断。理由是,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幅度如包括了可并处或单处某种附加刑的,如诈骗罪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针对该罪的基本犯罪构成规定的法定刑幅度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这时的附加刑是法定刑幅度中的最低刑,显然属已无减轻处罚刑罚空间的情况;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幅度如没有包括可并处或单处某种附加刑的,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不能单处附加刑,当然也就不能把附加刑作为减轻处罚的刑罚空间。
综上分析,上述裁判规则应是刑事立法的应有之义。在司法实践中直接适用刑法总则第三十七条于个案时,应严格遵守上述裁判规则。上述裁判规则的确立,既有效地限制了刑法总则第三十七条的随意适用;也厘清了刑法总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与第三十七条规定的逻辑关系,澄清了关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除刑事处罚”这一刑事立法科学含义和内在的规定性。
作者系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副院长
定减轻处罚情节,又无法定免除处罚情节的被告人予以免除处罚的案件,就更应报最高法院核准。但根据刑法总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对于没有法定免除处罚情节的被告人如果认为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予以免除处罚,法律并没有规定要报最高法院核准。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在这两个法条之间存在“逻辑冲突”呢?2005年9月5日《人民法院报》刊登梁剑《如何处理法条与逻辑之间的冲突》一文(下称“梁文”),肯定了“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的一些规定与做法存在违背逻辑的地方”,并且提出“既然法律对于减轻处罚、免除处罚的条件均作出了明文的规定,那么,我们在适用法律时就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法官在量刑时,即使被告人没有法定免除处罚情节,只要认为案件中的被告人的确符合免予刑事处罚的适用条件,就可以对被告人大胆地适用免予刑事处罚,而不必报最高法院核准。”笔者认为这种法条间存在“逻辑冲突”的观点值得商榷:
一是减轻处罚与免除处罚的性质不同,减轻处罚是认定构成犯罪后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判处刑罚;免除处罚是认定构成犯罪后不处罚。判处刑罚与不处罚是有原则区别的,尤其是某些严重犯罪,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法定最低刑很高,如“梁文”所谈及的张某绑架案,法定最低刑是十年有期徒刑,对被告人是做减轻处罚,还是做免除处罚,结果差别很大。在案件不具备法定减轻和免除处罚情节的情况下,如果减轻处罚,根据法律的规定不仅办案法官没有权力,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也没有权力,只有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而如果选择宽于减轻处罚的免除处罚,按照“逻辑冲突”观点简单认为的那样合议庭可以依法直接做出,而不用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不仅仅是逻辑冲突的问题,更重要是影响执法的统一,显失法律的衡平;
二是刑法总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其立法价值在于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维护罪刑法定原则。如果刑法总则第三十七条与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存在着逻辑冲突,不仅使刑法总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失去了立法价值,而且有可能导致刑事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把本应报最高法院核准做减轻处罚的案件,而做免除处罚,造成在实践中执法的不统一和法官恣意擅断的恶果;
三是如果刑事立法真的存在“逻辑冲突”,就意味着刑事立法存在严重疏漏,要么予以修改,要么通过作出司法解释的形式予以弥补,而不能留下如此严重疏漏让法官在司法实践中任意理解和适用,这有损于法律的权威和严肃。但是,到目前为止,立法机关和最高法院并没有对刑法总则第三十七条做出否定性评价或限制性的规定。
基于以上分析,说明“逻辑冲突”的观点并不成立,是对立法精神误读。笔者认为,纵观我国刑事立法结构、体系,刑法总则第三十七条与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具有内在联系,刑法总则第三十七条直接适用于个案,在特定的情况下要受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限制。主要理由阐述如下:
第一,法官所享有的刑事自由裁量权,是指在刑事审判中法官在一个合理范围内对案件自由地作出主观判断的权力,包括对案件事实如何认定、对于临界行为如何定性,以及如何合理量刑等问题进行处理等。从理论上讲,刑事自由裁量权,是有条件的、是要受到限制的。这个条件和限制就是必须“在一个合理范围内行使”。这个“合理范围”应是基于刑事法律的规定和刑事法律所蕴含的原则和精神,它是客观的,可衡量、把握和操作的,而不应是法官的主观臆断。具体到司法实践,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要受到如下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定的限制:从宏观上讲要受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原则的限制,即必须遵循罪之法定、罪名法定、刑之法定的原则;从微观上讲对具体案件的被告人裁量刑罚要受刑法分则规定的法定刑的限制;要突破法定刑,就要受刑法总则规定的法定量刑情节的限制;不具备法定减轻处罚的要减轻处罚要受刑法总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限制。由此形成对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法律约束。刑法总则第三十七条规定了“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从形式上看,法律并没规定适用的具体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官可以仅凭主观判断,不受限制地自由适用这一法律规定。理由是:
第二,从立法上看,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三类事由可以适用免除处罚:一是刑法总则针对犯罪的具体情节作出的“可以”或“应当”免除处罚的规定,这些具体情节包括:预备犯、中止犯、从犯、胁从犯、自首、立功及防卫过当和紧急避险过当构成犯罪等情节;二是刑法分则针对具体犯罪的特殊情节做出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的规定,包括刑法分则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的行贿人在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第三百五十一条规定的非法种植罂粟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在收获前自动铲除的、第三百八十三条规定的个人贪污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1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第三百九十条规定的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第三百九十二条规定的介绍贿赂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介绍贿赂行为的;三是刑法总则针对犯罪的综合情节做出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的规定,这就是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以上三类事由前两类是具体的、明确的,在执行中不发生争议。只有刑法总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则是原则的,看似法条没有具体规定适用的条件,可以由法官内心确信,自由裁量。实际是有条件的,只不过这种条件没有用具体文字明确规定在具体法条之中,而是蕴含在刑事立法结构和体系之中。
第三,纵观我国刑法分则立法结构,对大部分犯罪依犯罪情节分别规定了基本犯罪构成和加重(分为结果加重和情节加重)犯罪构成,并相应规定了基本罪法定刑幅度和加重罪法定刑幅度。对基本罪法定刑幅度的规定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法定刑幅度从高到低界定,如刑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的丢失枪支不报罪的法定刑幅度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法分则对社会危害性相对较轻的犯罪一般都采用这种从高到低的方法界定法定刑的幅度,只有故意杀人罪是例外;另一种是法定刑幅度从低到高界定,例如“梁文”涉及的案例绑架罪,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的法定刑幅度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采取这种方法规定法定刑的一般都是社会危害性相对较重的犯罪。再细分,从高到低界定法定刑幅度的,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所规定的法定刑幅度下限包含了刑罚体系主刑最低的刑种(管制),如诈骗罪,刑法规定的基本犯罪构成的法定刑幅度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另一种没有包括主刑最低的刑种,如前述的刑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的丢失枪支不报罪,法定刑幅度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法定最低刑不包括管制这一主刑最低刑种。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规律性认识:根据刑法分则对法定刑幅度规定的不同,有三种情况的犯罪存在减轻处罚的刑罚空间,1.适用加重罪法定刑幅度的犯罪。因为加重罪法定刑幅度是建立在基本罪法定刑幅度之上的。所以,基本罪法定刑都可成为该罪减轻处罚的刑罚空间;2.适用从低到高界定法定刑幅度的犯罪。因为我国刑法分则对犯罪采取从低到高界定法定刑幅度的,最低刑都是从三年有期徒刑起刑。所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都是减轻处罚的刑罚空间;3.适用从高到低界定法定刑幅度的犯罪,法定最低刑中没有包括主刑最低刑种(管制)的,管制刑就是减轻处罚的刑罚空间。只有在从高到低界定法定刑幅度中包括主刑最低刑种(管制)的,没有减轻处罚的空间。因为,管制刑是法定最低刑,法定最低刑以下就没有可判的刑罚(主刑)了。分析刑法分则对法定刑幅度规定呈现的这种特点,再结合刑法总则第三十七条和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笔者认为,对不具有法定减轻处罚和免除处罚情节的被告人予以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应遵守以下裁判规则:
1.法律规定的法定刑幅度存在减轻处罚的刑罚空间的,法官如果拟对被告人做减轻处罚,依法就要报最高法院核准;法官如果拟对被告人做宽于减轻处罚的免除处罚,因为中间跨着减轻处罚的刑罚空间,这种情况下的免除处罚,实际是在减轻处罚基础上做出的,理应受刑法总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制约,也要报最高法院核准。
2.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幅度不存在减轻处罚刑罚空间的犯罪,如果认为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才可直接适用刑法总则第三十七条,对被告人做免除处罚,而不必报最高法院核准。其一,这样做并不违背刑法总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立法精神,因为,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幅度不存在减轻处罚刑罚空间的犯罪;其二,这种情况下的犯罪均是轻微犯罪,即法定最低刑可以判处管制刑的犯罪,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节和社会危害性认为判处管制刑罚仍觉得过重的,只有适用刑法总则第37条判处免予刑事处罚了,这样做是法官对刑事自由裁量权的正当行使。
3.对适用加重罪法定刑幅度的犯罪和法定最低刑相对较高的犯罪(如前述绑架罪)在不具备具体的法定免除处罚情节的情况下,一般不应直接适用刑法总则第三十七条对被告人做宽于减轻处罚的免除处罚。这是因为,适用加重罪法定刑幅度的犯罪和法定最低刑相对较高的犯罪,构成这种罪的本身就说明被告人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性的严重。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性严重的犯罪又认定“犯罪情节轻微”而判处免除处罚,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也违背刑事立法的基本精神。当然如果案件特殊,确需做出免除处罚的必须报最高法院核准。
需要说明的是,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幅度是否包括附加刑不影响减轻处罚刑罚空间有无的判断。理由是,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幅度如包括了可并处或单处某种附加刑的,如诈骗罪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针对该罪的基本犯罪构成规定的法定刑幅度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这时的附加刑是法定刑幅度中的最低刑,显然属已无减轻处罚刑罚空间的情况;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幅度如没有包括可并处或单处某种附加刑的,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不能单处附加刑,当然也就不能把附加刑作为减轻处罚的刑罚空间。
综上分析,上述裁判规则应是刑事立法的应有之义。在司法实践中直接适用刑法总则第三十七条于个案时,应严格遵守上述裁判规则。上述裁判规则的确立,既有效地限制了刑法总则第三十七条的随意适用;也厘清了刑法总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与第三十七条规定的逻辑关系,澄清了关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除刑事处罚”这一刑事立法科学含义和内在的规定性。
作者系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副院长
三门峡律师|三门峡律师网:河南蓝剑律师事务所 版权所有 备案号:豫ICP备10207368号-1
地址:河南省三门峡市商务中心区明珠大厦12楼 邮政编码:472000 电话:0398-3690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