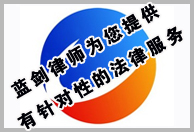杨迎春----浅议 “亲亲相隐”
在现实生活的宣传中,面对有违法犯罪的亲人,人们不由自主的赞赏大义灭亲,对不举报甚至帮助自己亲人的行为施以包庇罪的刑事处罚。但面对这个问题,到底是大义灭亲还是隐瞒更符合人性本身和社会道德呢?这个问题上升到法律层面有两点表现,第一面对亲人犯罪,作为一个知法懂法之人应不应该隐瞒。第二面对亲人之间隐瞒窝藏罪犯的行为,法律应当怎样审判窝藏人。这样的法律与亲情道德的冲突问题,我国解决方式自古就有,其名为“亲亲相隐”。
在古代,为了维护伦理纲常和家族团结,“亲亲相隐”成为古代刑律的一项基本原则,其内容为:亲属之间有罪应当互相隐瞒,不告发和不作证的不论罪,反之举报则要论罪。亲亲相隐最早为春秋时期孔子提出,后来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得到进一步确认,一直到唐以后基本定型,其具体规定有三点:第一亲属有罪而隐,不论罪或减刑。第二控告应相隐的亲属要处刑。第三谋反谋逆谋叛等某些重罪和某些亲属互相侵害罪不适用亲亲相隐。可见唐以后的这一原则已经变得非常完备。
首先,就亲亲相隐的形成来说,最早见于《论语•子路》其文为: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其意为:叶公告诉孔子说:“我的家乡有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就告发了他的父亲。”孔子说:“我家乡的正直的人和你讲的正直的人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可见孔子所推崇的“直”并非是刚正不阿,容不得任何情意牵连,而更多的是对父慈子孝,家族内部信任团结的一种推崇和鼓励,这切合于人性天理,体现了孔子对法律容情的恻隐之心。
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孔子所有思想的立足点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也就是说“亲亲相隐”是有等级区别的,这也就是接下来笔者关于上述唐律第二点规定不合理性的探讨。唐律第二点规定:控告应相隐的亲属要处刑。什么样的亲属属于应相隐的亲属呢?怎么处刑呢?《唐律疏议》中规定:“诸同居,偌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其事及擿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这里容隐的亲属包括大功内的父母子女、夫妻、祖孙,更包括不同居的同姓大功以上的亲属及外祖父母、外孙、孙媳、夫之兄弟、兄弟妻等。除此之外,奴婢或仆人为主任隐匿犯罪也不处罚。其他不同居的小功以下的亲属如果隐匿犯罪,较之普通人降三个等级进行减轻处罚。但是唐代《斗讼律》又规定:“子孙告祖父母、父母者,绞。”同时还规定,如父祖告子孙、外孙、子孙之妻妾或自己的妾的,无论告得实还是诬告都不处罚。可见古代刑律关于“亲亲相隐”的平等性,以下犯上者重罪。另《左传》讲述了一个事件:齐国的臣子石碏扮演惩恶的角色设计杀死了自己的儿子石厚。《左传》对此赞叹说:“大义灭亲,其之谓乎!”《吕氏春秋》也记载了墨家一位领袖腹朜,他的儿子杀了人,秦惠王对他说:“先生你的年事已高,又没有别的儿子,寡人已经命令官吏不杀你的儿子了,先生这件事你就听我的吧。”腹朜不听惠王的,还是杀了儿子。《吕氏春秋》评价:“忍所私以行大义,巨子可谓公矣。”除了这两个典型大义灭亲的例子,还有包拯斩侄等很多类似例子,这些例子突出的典型特征就是:古代的“大义灭亲”是单向的,父母对子女,丈夫对妻妾。而父母有罪过,子女以大义而诛杀的事例几乎没有。可见古代“亲亲相隐”正当性在于卑幼隐瞒尊长的过错罪行,促使其逃脱刑罚,从而保全家庭,这体现了亲情人伦。其不合理性在于尊长有权管教卑幼,也有资格揭发卑幼的犯罪,卑幼被附加了一种不得不隐的强制义务,而尊长被赋予了一种自由裁量的权利。这在现代的民主平等社会简直无法想象,“亲亲相隐”原则在现代法律中适用必须予以发展改造,符合民主平等的要求。
谈了中国古代的“亲亲相隐”,我们回顾西方法制史,也不难看到“亲亲相隐”的表现,即容隐权。1810年《法国刑法典》规定:知晓近亲属犯罪而不告发、为亲属做伪证、帮助亲属逃脱等均不受处罚。而且这一容隐制度的规定在西方一直绵延至今,如1994年的《德国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近亲属可以拒绝作证;即使自愿作证也有权不宣誓担保证词无伪,证人可以拒绝回答可能使自己的近亲属负刑事责任的问题。与上述列举的大陆法系国家相比,英美法系国家虽然在容隐权范围上大幅缩减,但仍然保留容隐制,如英美法律规定夫妻隐匿罪行免刑。
回到当今我国法学界,《刑法》关于窝藏、包庇罪的规定是这样的: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款罪,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这里对行为人的身份并没有作出限制,可见当代我国的法律已经将“亲亲相隐”的原则完全舍弃。本着现代法律价值,从维护国家司法权的有效行使来看,无疑是必要的。但是从现代法治精神来看,它又完全背离以人为本的伦理道德。保护亲人是人之本性,父母为保护子女甚至不惜生命,对父母窝藏包庇子女定窝藏罪是对人性的践踏,对道德的漠视。明知道父母不可能不包庇子女的罪行而对父母定罪,这样的法律规定有何意义呢?我国的刑法过于重视国家本位,而忽视了法律中的伦理价值和人性诉求。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因为犯罪过多而崩溃,而有许许多多的国家因为道德沦丧而毁灭。作为当代法律人,我们希望将“亲亲相隐”的传统继承到现代法律中来,虽然其具有一定弊端,但只要我们加以改造,必能使人性与法性相融和,法律与道德相适应,使我国的法律体系更加完善合理,使依法治国的进程有效推进。
- 上一篇:王欣欣----我们是快乐的一家人
- 下一篇:赵芮----写在2015
三门峡律师|三门峡律师网:河南蓝剑律师事务所 版权所有 备案号:豫ICP备10207368号-1
地址:河南省三门峡市商务中心区明珠大厦12楼 邮政编码:472000 电话:0398-3690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