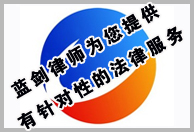闫永成——漫谈法治
法治是政治文明最坚实的基础。无论在古希腊、古罗马、古中国,理解法之治是所有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基本功。
法律和法治是两回事。法律可能倾向左派,也可能倾向右派;可能倾向强者,也可能倾向弱者。法治则是让法律成为治理国家最高权威的手段,是迫使政府守法的手段。
当人类拥有了政府——垄断所有暴力手段的管理社会的机构,人类社会就摆脱了野蛮的丛林法则,进入了“文明社会”。在“文明社会”里,政府是对人民福利最大、最直接的威胁,限制政府滥用公权成为推进“政治文明”的永恒难题。
政治文明指的是政府依照“基本法”来行使权力。“基本法”不是眼下的人“制定”的法,而是人类社会在长期的痛苦实践中“形成”的六条普遍行为准则。这准则非常简单,也非常抽象,就是禁止杀戮、偷窃、抢劫、欺骗、遗弃、滥淫。禁止“遗弃”就是不许抛弃弱者,特别是丧失了劳动能力的老人;禁止“滥淫”是要求人类的性活动受一定限制,比如不能强奸,不能与近亲和未成年幼女性交。
为什么要法治?法治的根本目标不是治民,而是治吏,是治理政府,是限制政府官员“胡作非为”。
无论对中外的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政府官员滥用权力都是噩梦。基于历史经验,几乎所有学人都认为,法之治强于人之治。人有私欲,将公权托付于“人”总不保险,所以法之治强于人之治。
有些民主主义者反对法治与人治的区别,说“人之治”乃是大不相同的,少数人和多数人不同,少数人的代表和多数人的代表不同。其实,仔细想想,少数和多数的界限并不清楚,都是相对的,因为社会不可能只分成两个利益集团。在现实政治制度里,相对多数决基本上也是相对少数决。不仅如此,多数人之治、少数人之治,都是人治,都未必守法。以相对多数来欺负相对少数,或者以相对少数来欺负相对多数,都违背了法治精神。
真正的问题是:政府及政府官员为什么要尊重法律?人都有欲望。垄断了所有暴力手段的政府官员们为什么要给自己的欲望制造不便,限制自己的自由,依照法律来治国?在法律与政府官员的私欲、方便、或雄心壮志发生冲突时,他们会遵守法律吗?如果政府官员经常不守法,明明白白的“文”不受政府尊重,就没有“政治文明”。
为了建设一个行为受法律约束的政府,我们自然得到三个问题:第一,政府为什么会遵守法律?第二,谁来判定政府违法,第三,谁能惩罚违法的政府?
第一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如果政府违法会遭到严厉惩罚,那么政府就会敬畏和遵守法律。这与老百姓敬畏和遵守法律的道理是一样的。
在西方的传统社会还有另一种回答。法来自神与人定的契约,神是至高无上的,违法会遭“神谴”,因此政府会敬畏法律。神权是一种权力,对世俗权力构成制约。然而,当政府以神的名义滥施暴政,人民很难判定什么是神的真正意志。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也有另一种回答。法来自道德。如果政府官员受儒家道德思想熏陶,尊奉儒家思想,就会贤明有德,就奉公守法。然而,当政府以道德的名义滥施暴政,人民很难判定什么是真正道德的。
中国传统的“德政”与西方传统的“神政”实质上都是某种限制和惩罚政府的手段,也都起到过让政府守法的作用。但神的意志或者道德限制都可以有相当宽泛和弹性的解释,何况政府努力掌握解释的“权威”。所以,无论“德政”还是“神政”,均难避免政府滥施暴政,于是两地的历史上都常出现“苛政猛于虎”的现象。
当“市场的社会”(亦称“商业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降临以后,竞争就成为市场社会里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在市场条件下,“德政”和“神政”都变得苍白无力了,西方的“哲君”或者中国的“圣王”越来越鲜见。市场机制决定,生存与激烈的竞争密切相关。在竞争的社会里,对物质利益的信仰远远超出了对神或道德的信仰,宗教和道德势力就衰落了。政府官员可能会敬畏神,也可能敬奉“为人民服务”的道德。但在市场的社会里,对神和道德的信仰都变得极不可靠。
我们只好回到我们的基本假设:如果政府违法会遭到严厉惩罚,政府就会敬畏和遵守法律,就有法治。
可谁来判定政府违法,谁又能惩罚垄断了暴力手段的政府呢?能惩罚政府的社会岂不就是无政府状态?对这个问题的出色理解代表西方政治文明最伟大的成就。
如果“权力只能被权力来制约”,那么,只有相当的权力能相互制约,只有政府的权力才能制约政府的权力。
人民的选举能产生政府权力,但很难制约政府权力,更未必能迫使政府守法。
人民的权力当然不可能与政府相匹配。如果“人民的权力”与政府的权力相当,政府就成为不必要的东西了。人民若干年才享受一天的选举,不可能每日每时都在限制政府权力。因此,在缺少法治的国家,我们能看到民选的总统经常是喊着反腐败上台,然后在腐败中下台。如果民选了若干总统都腐败,为什么我们会认为下一个民选总统不会违法,不会腐败呢?不仅如此,民主选举表达相对多数对“自己人”的支持,未必是对法律的支持。人民组成集团去选举立法者和行政领袖,当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自己集团的利益,不是为了让自己的领袖遵守统一的法律。多数决未必决定支持法律。
分权制衡的思路可以追溯到两千五百年前的古希腊以及两千年前的古罗马。分权制衡成为比较成熟的制度还要首推近代的英国。当美国有了最高法院,首创了“违宪审查”制度,分权制衡就达到了辉煌的顶峰。
什么是“违宪审查”?违宪审查指的是:最高法院(或者宪法法院)的法官有权按照《宪法》来判案,决定议会制定的法律和政府制定的行政条例违反宪法,判决其失效。
法治思想之所以出色,在于让“人”(政府各部门)的权力互相掣肘,从而使“法”的权威上升,迫使政府严格依法行政。因此,“法”之所以能“治”,在于政府内部的分权制衡,特别是司法独立;在于由一个中立的、职业的机构来判断立法和行政决策是否违反了《宪法》。
什么是法治?法治是让基本法的权威高于政府权威,迫使政府依《宪法》行政的制度。法之所以能“治”,在于三大基本原则:(1)基本法至上,即依(宪)法立法原则;(2)司法和公务员执法体系独立,即政府内部分权制衡原则;(3)司法和执法官员的“绩优”选拔和考评制度,即公正廉明原则
为什么依法立法、分权制衡、公正廉明三大原则导致法治,能迫使政府敬畏和尊重法律?
第一原则告诉当前的立法者不能任意立法,无论他们声称自己所立的“法”出自多么美好的目的,都必须符合一项几乎不可更改的至高“法律”。这是正义的基础,也是司法权威的根基,与眼下支持者的人数多少无关。
然而,如果没有第二个原则,基本法至上不过是空中楼阁。欲保障基本法或者《宪法》至高无上的地位,司法机构必须独立于行政决策和立法机构。不独立于决策者和人民,就不可能中立。只有独立的司法才能相对中立地判断立法和行政领袖是否违法。执法机构的相对独立性也是重要的,其目的是,(1)拒绝行政决策者的违法行政;(2)保证在不利于行政决策者和立法者之际,司法判决仍能得到执行。
然而,如果没有第三个原则,司法独立站不住脚。与民选的行政决策者和立法者不同,司法机构并没有民众势力的权力基础,看上去是最软弱的机构。有了法官对宪法乃至基本法的忠诚和深刻理解,司法机构才能同民选的立法和行政决策者相抗衡,才能得到官民双方的尊重。权力指的是支配别人的能力。权力的内容丰富多彩,包括赤裸裸的暴力、明晃晃的财富、也包括主观的思想意识形态、乃至人格的魅力。中国的古训说,“公生明,廉生威”。一心为公、不偏不倚、廉洁自爱、知识广博、光明正大,司法机构就有了权力。“公正廉明”本身就是权力基础。公正廉明来自这样一批社会精英:法官是终身职业,依照“绩优”(meri原则升迁,其职业生涯不断地经历选拔和考评,以至资历成为升迁的基本要素。英国法官至今戴白色假发套判案,提醒其认真行“长者”之权方能受尊重。司法独立必须成为原则,但司法独立地位的保障是公正廉明,是智识,是严格按照“绩优”原则进行不断的考试和考核,考察法官对法律的理解,考察其司法实践的成绩。
分权、司法独立,是制衡的必要条件,但还不足以导致严密的制衡。制衡还取决于分立的权力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功能重叠,比如行政和司法机构有一定的立法权,立法机构有一定的行政和司法权。到目前为止,人类对政治文明最基本的理解是:政府,无论是倾向“左派”还是“右派”的政府,都不能恣意妄为,必须被限制住,必须受基本法约束,受《宪法》约束,受法律约束,照“规矩”办事。
- 上一篇:赵建烈——父 亲
- 下一篇:杜文静——向日葵女生
三门峡律师|三门峡律师网:河南蓝剑律师事务所 版权所有 备案号:豫ICP备10207368号-1
地址:河南省三门峡市商务中心区明珠大厦12楼 邮政编码:472000 电话:0398-3690909